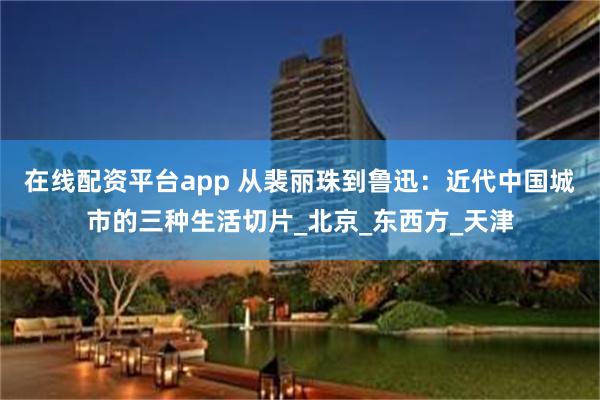
晚清至民国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时代变迁,北京的城墙、天津的租界、上海的里弄都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这当然是从大处着眼。如果从具体生活这一角度切入,则微观层面的细节会带给我们理解历史的更丰盈的感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裴丽珠的《北京纪胜》、李来福的《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及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鲁迅上海生活志》,穿透了表面的互不相关、各有主题在线配资平台app,于内在肌理上有了交叠的意义。
裴丽珠的北京情缘
裴丽珠何许人也?听说过她名字的读者恐怕不多,但提到另一个名字罗伯特·赫德,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这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之久,将中国的关税大权操弄于股掌之间。裴丽珠和赫德有关联吗?还真有,裴丽珠的父亲裴式楷(Robert Edward Berdon)是赫德的妻弟。东方式人情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西方也一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任用亲友,培植私人势力,将裴式楷从英国召至中国,进入大清海关,步步高升,做到副总税务司的高位。
裴丽珠是裴式楷的独生女,1881年生于中国,幼年和父母在汉口生活,1897年随父亲搬到北京,在这里一住40年,成了一名地道的“老北京”。
1920年,裴丽珠出版过一本书《北京纪胜》,此后多次再版,享有盛誉,林语堂盛赞其为“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从内容看,《北京纪胜》将北京的城墙、城门、宫苑、园林、寺庙、自然风景乃至生活景观一一道来,相当于一本游记。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
展开剩余85%《北京纪胜》,[英]裴丽珠 著,季剑青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
首先是文笔很出色。裴丽珠在序言里说,读者翻阅这本书,会产生一种作者“挽着你胳膊”逛遍北京及其郊区的感觉。可见她十分注重阅读体验,想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更重要的,是姿态和视角。
本书译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季剑青指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将北京视作典型的“东方奇观”,他们建构的北京形象充斥着经过西方滤镜装扮的异域风情,目的在于凸显前现代的中国与现代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北京看起来独特,其实很大程度上出自西方游客的想象与投射。
裴丽珠不一样。她的文字很少带有猎奇色彩,相反,她试图发掘北京和欧洲城市的共性。她写北京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说“如同伦敦的鱼贩子和巴黎的四季商人那般悦耳”;写清朝官员坐轿子出行的阵仗,用“伦敦的市长巡游”作对比;记录赶大车的风趣俚语,说他们有着“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这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写作策略,有助于让对东方一无所知的西方游客借助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快速了解北京;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她对北京的真爱。
晚清民国时期北京(1928年更名为北平)的外国人,以外交官及其家属、传教士、教师为主,他们大多住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同本地的人和事没有太深的勾连。裴丽珠则是真心热爱北京。她熟悉古都的风土人情,还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能和普通市民深入交流。因为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她也是北京社交圈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凡此种种,使北京对裴丽珠来说不构成奇观或异域,而是生活和精神上皆有紧密连接的第二故乡。作家写故乡,笔下自会流淌出细腻的爱和贴近的体会。这并不是说裴丽珠看不见东西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她当然看得见,但不会居高临下地评判。而且面对美好事物,她会遵从人类的爱美天性,由衷地发出赞美。此种真诚的态度,难能可贵。
1937年夏初,裴丽珠和丈夫去日本度假,期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突燃的战火阻断了归途,裴丽珠只得辗转前往美国。是年底,她因心脏病突发在旧金山辞世,享年56岁。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翌年将北京更名为北平,此举极大削弱了北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其变成了一座普通城市。同时随着政府机关南迁,众多官员、社会名流离开,经济也遭受打击。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后,官方重新界定北京的身份,借助“帝都遗存”,将其定位为“文化城”。这与《北京纪胜》的内容高度匹配。裴丽珠介绍了中南海、景山、天坛、国子监等人文景观,她对街头巷尾的描摹,更显示北平还拥有丰富的市井文化和浓郁的烟火气。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北京纪胜》作为游记的指南功能已消退,却仍有阅读价值——它留存了旧日北京的样貌与气息,从而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人类学记录。
丹麦工程师和近代天津
如果说晚清民国的北京/北平还是一座非常传统的中国城市,那么距离其120公里的天津则是另一番景象。
天津是近代中国较早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1860年英国率先在天津设立租界,顶峰时天津共有九国租界,总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这固然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租界当局也给传统中国吹入新风,比如开展市政建设,创办银行、企业、教堂、学校、医院等,将天津带入现代化进程。至19世纪末,天津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北方金融中心及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了。
关于外国人在近代天津的活动,学界更多注意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另一个小众群体丹麦人则被忽视。这也不难理解,比起英法德等列强,国小民寡、在天津又没有租界的丹麦确实没什么存在感。但这不代表丹麦人缺席了。丹麦汉学家、哥本哈根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来福翻遍丹麦国家档案馆、天津档案馆,撰写了《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一书,聚焦晚清时期天津丹麦人的工作与生活。
《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丹]李来福 著,刘海岩 龚 宁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从1860年到1912年的半个多世纪里,有大约150名丹麦人定居天津,他们受雇于租界当局或商业机构,充当工程师、商人、水手等。李来福重点观照工程师的作为。据他研究,这些丹麦工程师对天津乃至中国的现代市政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1871年来华的卡尔·璞尔生,曾为大清电报总局下辖的电报学堂编写教材,帮清政府培养通信人才;为盛宣怀主管的天津电报局安装电话线,推动中国电话事业发展。另一位工程师劳里茨·安德森参与过海河治理工程,还设计了天津最早的现代化下水道系统。
除了工作,李来福还勾勒出一幅生活图景。例如,在璞尔生的建议下,他的弟弟也来到中国发展,在海关任职。兄弟俩后来娶了当地欧洲侨民家庭的女子为妻,住在英租界的一栋西式洋房里。他们用欧式家具,过欧式生活,但餐桌上也会出现中式菜肴。兄弟俩的孩子在华洋杂处的环境里长大,既会说丹麦语和英语,也能用天津话作简单交流。
遗憾的是,因资料有限,《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整体写得比较简单,人物故事按粗线条展开,缺少细节的丰盈。这当然是求全责备。毕竟,书中人都是凡夫俗子,能在档案里留下痕迹就不错了,岂能奢望?十多年前有过一本《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作者布莱恩·鲍尔是在天津出生并长大的英国侨民,所述的租界风貌颇可一观,可与本书相互映照。
鲁迅的烟火上海
事实上,近年来这类从生活史角度观察和书写中国城市的著作出过不少。例如,三峡大学教授胡俊修的《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聚焦民国武汉的都市社会和大众娱乐。澳门大学历史学教授王笛那本备受赞誉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透过茶馆这一“微观世界”,描绘了成都几十年间的变迁。至于上海,更是凭借丰富的史料成为研究富矿,甚至发展出了“上海学”。
有关近现代上海生活的书已是俯拾即是,这里我推荐一本比较特别的——《鲁迅上海生活志》。
《鲁迅上海生活志》,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年出版
作为现代中国文坛“天王巨星”级别的人物,鲁迅研究自成一门显学,其生平、作品、思想早就被翻来覆去解读了个遍。不过,或许由于星光耀眼,反而遮蔽了日常性的一面。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住在哪儿?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并呈现给公众的。
这方面,上海鲁迅纪念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馆至今70多年,其收集了大量与鲁迅有关的物质材料,足以为鲁迅及其家人勾勒出一部上海生活史。汇聚众多研究者编写的《鲁迅上海生活志》,正是这样一部书。
该书以纪念馆保存的鲁迅生活遗物为研究对象,分为“书房一隅”“寻常烟火”“休憩时刻”“此中甘苦”“居于沪上”等五部分。涉及的物品可谓琳琅满目,除了一般文化人都有的印章、信笺、藏书、墨砚、书橱等,还有冰箱、衣物、家庭常备药等。从诸多细节可以推断出,无论鲁迅对“海派”持何种态度,他和家人已深度嵌入海派生活之中。
鲁迅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已是众所周知,读了这本书,我还有新发现。例如,从前我只知道鲁迅爱喝家乡绍兴的黄酒,读了邢魁的文章,才发现他也常喝啤酒,甚至喝葡萄酒、威士忌;吴仲凯则描绘了一个爱吃糖的鲁迅,既爱柿霜糖、核桃糖等中式糖食,也爱水果糖、柠檬糖、朱古力等外国糖食;郑亚聚焦馆藏的11件花瓶,告诉我们鲁迅有很高的审美品位,这和萧红笔下那个对色彩敏感、对穿搭颇有心得的鲁迅恰可互相印证。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上海生活志》将鲁迅还原成为周树人——他不再晦涩难懂,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曾行走于世间的人。
如果说裴丽珠笔下的北京,是挽着胳膊带你感知日常的温度与人性,丹麦工程师在天津的足迹,是现代化浪潮中异国工匠嵌入城市血脉的无声凿痕,那么鲁迅遗物构筑的上海生活志在线配资平台app,让我们得以窥见文化巨擘在都市烟火中的真实侧影。这些散落的历史碎片,如同穿越时空的棱镜,折射出近代中国城市多元、复杂而充满张力的面貌。
发布于:上海市